悲觀有一樣好處,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了一些。這個可也就是我的壞處,它不起勁,不積極。您看我挺愛笑不是?因為我悲觀。悲觀,所以我不能扳起麵孔,大喊:“孤——劉備!”我不能這樣。一想到這樣,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。
看著別人吹胡子瞪眼睛,我從脊梁溝上發麻,非笑不可。我笑別人,因為我看不起自己。別人笑我,我覺得應該;說得天好,我不過是臉上平潤一點的猴子。我笑別人,往往招人不願意;不是別人的量小,而是不象我這樣稀鬆,這樣悲觀。
我打不起精神去積極地幹,這是我的大毛病。可是我不懶,凡是我該做的我總想把它做了,總算得點報酬養活自己與家裏的人——往好了說,盡我的本分。我的悲觀還沒到想自殺的程度,不能不找點事作。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,那隻好死嘍,我有什麼法兒呢?
這樣,你瞧,我是無大誌的人。我不想當皇上。最樂觀的人才敢作皇上,我沒這份膽氣。
有人說我很幽默,不敢當。我不懂什麼是幽默。假如一定問我,我隻能說我覺得自己可笑,別人也可笑;我不比別人高,別人也不比我高。誰都有缺欠,誰都有可笑的地方。
我跟誰都說得來,可是他得願意跟我說;他一定說他是聖人,叫我三跪九叩報門而進,我沒這個癮。我不教訓別人,也不聽別人的教訓。
幽默,據我這麼想,不是嬉皮笑臉,死不要鼻子。
也不是怎股子勁兒,我成了個寫家。我的朋友德成糧店的寫帳先生也是寫家,我跟他同等,並且管他叫二哥。既是個寫家,當然得寫了。“風格即人”——還是“風格即驢”?——我是怎個人自然寫怎樣的文章了。
於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寫家。我不以這為榮,也不以這為辱。我寫我的。賣得出去呢,多得個三塊五塊的,買什麼吃不香呢。賣不出去呢,拉倒,我早知道指著寫文章吃飯是不易的事。
稿子寄出去,有時候是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頭;連個回信也沒有。這,咱隻好幽默;多喒見著那個騙子再說,見著他,大概我們倆總有一個笑著去見閻王的,不過,這是不很多見的,要不怎麼我還沒想自殺呢。
常見的事是這個,稿子登出去,酬金就睡著了,睡得還是挺香甜。直到我也睡著了,它忽然來了,仿佛故意嚇人玩。數目也驚人,它能使我覺得自己不過值一毛五一斤,比豬肉還便宜呢。
這個咱也不說什麼,國難期間,大家都得受點苦,人家開鋪子的也不容易,掌櫃的吃肉,給咱點湯喝,就得念佛。是的,我是不能當皇上,焚書坑掌櫃的,咱沒那個狠心,你看這個勁兒!不過,有人想坑他們呢,我也不便攔著。
這麼一來,可就有許爭人看不起我。連好朋友都說:“夥計,你也硬正著點,說你是為人類而寫作,說你是中國的高爾基;你太泄氣了!”真的,我是泄氣,我看高爾基的胡子可笑。他老人家那股子自賣自誇的勁兒,打死我也學不來。
人類要等著我寫文章才變體麵了,那恐怕太晚了吧?我老覺得文學是有用的;拉長了說,它比任何東西都有用,都高明。
可是往眼前說,它不如一尊高射炮,或一鍋飯有用。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“人類改造丸”,我也不相信把文學殺死便天下太平。我寫就是了。
別人的批評呢?批評是有益處的。我愛批評,它多少給我點益處;即使完全不對,不是還讓我笑一笑嗎?自己寫的時候仿佛是蒸饅頭呢,熱氣騰騰,莫名其妙。及至冷眼人一看,一定看出許多錯兒來。我感謝這種指摘。說的不對呢,那是他的錯兒,不幹我的事。
我永不駁辯,這似乎是膽兒小;可是也許是我的寬宏大量。我不便往自己臉上貼金。一件事總得由兩麵瞧,是不是?
對於我自己的作品,我不拿她們當作寶貝。是呀,當寫作的時候,我是賣了力氣,我想往好了寫。可是一個人的天才與經驗是有限的,誰也不敢保了老寫的好,連荷馬也有打盹的時候。
有的人呢,每一拿筆便想到自己是但丁,是莎士比亞。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,天才須有自信的心。我可不敢這樣,我的悲觀使我看輕自己。我常想客觀的估量估量自己的才力;這不易做到,我究竟不能像別人看我看得那樣清楚;好吧,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,也就不用裝蒜,謙虛是必要的,可是裝蒜也大可以不必。
對作人,我也是這樣。我不希望自己是個完人,也不故意的招人家的罵。該求朋友的呢,就求;該給朋友作的呢,就作。作的好不好,咱們大家憑良心。所以我很和氣,見著誰都能扯一套。
可是,初次見麵的人,我可是不大愛說話:特別是見著女人,我簡直張不開口,我怕說錯了話。
在家裏,我倒不十分怕太太,可是對別的女人老覺著恐慌,我不大明白婦女的心理;要是信口開河的說,我不定說出什麼來呢,而婦女又愛挑眼。男人也有許多愛挑眼的,所以初次見麵,我不大願開口。我最喜辯論,因為紅著脖子粗著筋的太不幽默。
我最不喜歡好吹騰的人,可並不拒絕與這樣的人談話;我不愛這樣的人,但喜歡聽他的吹。最好是聽著他吹,吹著吹著連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麼地方去,那才有趣。
可喜的是有好幾位生朋友都這麼說:“沒見著閣下的時候,總以為閣下有八十多歲了。敢情閣下並不老。”是的,雖然將奔四十的人,我倒還不老。
因為對事輕淡,我心中不大藏著計劃,作事也無須耍手段,所以我能笑,愛笑;天真的笑多少顯著年青一些。
我悲觀,但是不願老聲老氣的悲觀,那近乎“虎事”。我願意老年輕輕的,死的時候象朵春花將殘似的那樣哀而不傷。我就怕什麼“權威”咧,“大家”咧,“大師”咧,等等老氣橫秋的字眼們。
我愛小孩,花草,小貓,小狗,小魚;這些都不“虎事”。偶爾看見個穿小馬褂的“小大人”,我能難受半天,特別是那種所謂聰明的孩子,讓我難過。
比如說,一群小孩都在那兒看變戲法兒,我也在那兒,單會有那麼一兩個七八歲的小老頭說:“這都是假的!”這叫我立刻走開,心裏堵上一大塊。世界確是更“文明”了,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,可是我還願意大家傻一點,特別是小孩。假若小貓剛生下來就會捕鼠,我就不再養貓,雖然它也許是個神貓。
我不大愛說自己,這多少近乎“吹”。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。
不過,剛過完了年,心中還慌著,叫我寫“人生於世”,實在寫不出,所以就近的拿自己當材料。萬一將來我不得已而作了皇上呢,這篇東西也許成為史料,等著瞧吧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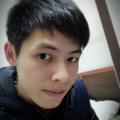 嚇倒三千軍
嚇倒三千軍

